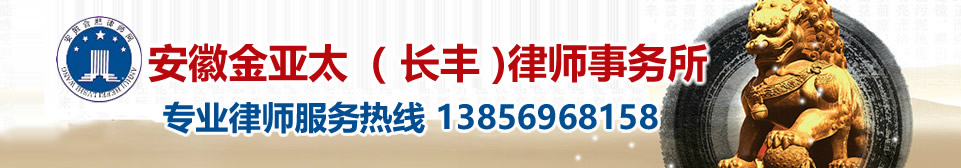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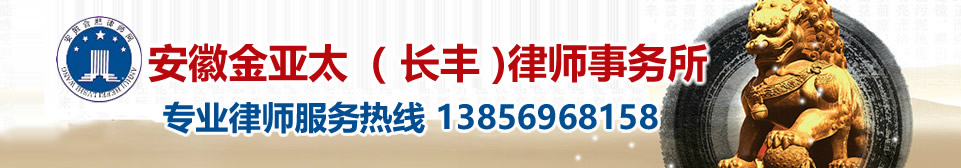
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故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比更具有运用刑法进行规制的必要性。然而,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和刑法的三个法律条文即可奏效,而是需要一个有效的刑法规范体系。对现行刑法规范体系的完善,关键在于构建立体化的刑法规范体系,使之既有前置性、预防性的规范,又有惩罚性、后置性的规范,并且与行政法规无缝衔接。
(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模式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体系本无争议,但由于在2011年2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439名人大代表共同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故出现了是否需要制订特别刑法的争议。从我国目前的立法实况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己然形成。作为七大部门法之一的刑法,其立法模式是统一的、集中的刑法典模式。同时,无论是《食品安全法》,还是其他类似行政法,都是在明确规定具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后,以“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来衔接刑法。因此,制订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特别刑法既与现行刑法立法模式相冲突,也无实际必要。当然,出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重要性的认识,完全可以在现行刑法立法模式下在刑法分则第二章或第三章内设专节规定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
如果在刑法分则中设专节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那么应当在现行基本犯罪和延伸犯罪的基础上增设相关罪名等,以此完成罪名设置层面的完善。
1.增设新罪名。现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之所以滞后,主要原因在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的不匹配。例如:《食品安全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而对系列主体规定了如召回不安全食品等系列义务,但刑法未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将不作为规制为犯罪,更未将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故应当增加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等不作为型犯罪,以促使生产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召回,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
值得探讨的是食品的定义。食品的定义直接影响到准确定罪量刑。《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定义为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同时,《食品安全法》又将食用农产品定义为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将食品添加剂定义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由此可知,《食品安全法》所指的食品不包括食用农产品和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法》之所以将食品与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并列,原因在于食用农产品已由其他法律予以规制,而食品添加剂对于食品相当重要,故予单列出来以使其享受与食品相同的保护力度。然而,从大众观点来看,食品是指一切可供食用的物品,故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是应有之义,而作为食品的原料或者辅料之一的食品添加剂也理所当然地应当包括于食品范畴中。如果刑法中的食品定义采用前一种观点,那么完全应当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专节中增设诸如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相关产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相关产品罪等罪名。否则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的相关产品(如: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只能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论处,与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宗旨背道而驰。如果刑法中的食品定义采用后一种观点,那么就应当重新定义刑法中的食品。从刑法本身而言,除了信用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解释方式确定概念外,尚未对类似于食品等定义做出相应解释。通常的做法是按法理借用其他法律的概念性规定,如何谓枪支、淫秽物品等。因此,刑法中的食品定义应当以《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定义为基础,并予以适当扩张。因此,刑法中的食品是指:供人食用或饮用的成品,包括制作成品的原材料、可以直接食用的农产品、食品添加剂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包装视为食品的组成部分。
2.将犯罪预备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现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预防性却体现得不够。即使《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基本法定刑修改为危险犯,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基本法定刑修改为行为犯,但仍然面临着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调控不力的危机。这主要体现在刑法对部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入罪。将犯罪预备行为入罪,意味着刑法介入时间的提前,也意味着扩大了犯罪圈。然而,由于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时存在一个证明主观明知的难题,即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之目的,因此,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刑法规制也存在疑问。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预备行为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预备行为都难以证明其主观目的。从客观而言,如果生产者为降低生产成本而购入了变质食品或有毒有害的原料,而且购入这些原料或食品除了用于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外别无他用,或销售者为了牟取暴利而低价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且购入这些食品除用于销售外别无他用,那么其犯罪的主观目的还是比较容易证明的。因此,对于为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购入问题原料,或者为了销售而大量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当前愈演愈烈的塑化剂风波告诉我们,千万不能指望通过现有刑罚的有限威摄力来防止出现类似于塑化剂食品等严重事件发生,而是应当将涉及食品安全的犯罪圈扩大化,将危害食品安全的预备行为入罪。
3.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修改
(1)犯罪对象。从本罪罪状表述来看,其犯罪对象为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所形成的有毒、有害食品,而非所有有毒、有害食品都系本罪的犯罪对象[1]。然而,从罪名来看,本罪的犯罪对象为所有有毒、有害食品,与罪状表述名不副实。从逻辑而言,有毒、有害食品一定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因此,如果食品本身天然具有毒害,或者是因掺入有毒、有害的食品原料造成,在不能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论处的情况下,则只能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论处。例如:将河豚鱼作为菜肴予以销售,造成食客中毒死亡。在排除故意杀人的情况下,一般只能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论处。究其原因就在于河豚鱼并非因人为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所形成的有毒、有害食品,而是天然有毒食品。从对人体健康的威胁程度来看,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显然轻于有毒、有害食品,故而刑法也相应配置了较轻的刑罚。然而,如果将上述河豚鱼与甲荃血旺进行毒性比较,虽然前者毒性大于后者毒性,即前者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大于后者,但生产、销售前者只能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论处,而生产、销售后者却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论处,这显然是一个轻重倒置的错误,是立法者在对本罪犯罪对象做出严格的限制的同时未考虑周延。要解决上述问题,出路在于扩大本罪犯罪对象的范围,即扩大到所有有毒、有害食品。凡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皆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论处。只有这样,才能让本罪名实相符。
(2)罪状表述。本罪罪状表述的另一缺陷在于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来源限定为掺入。那么如果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是渗入的[2],或者是涂抹的,是否应该以本罪论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比较上述三种行为,它们的实质均为在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只不过在添加的具体方式上有所不同。因此,应当将本罪的“掺入”修改为“掺入、渗入、涂抹”。同时,也要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添加行为都应当与掺入行为并列,例如注射。一般而言,注射行为系由除生产者、销售者之外的他人出于危害公共安全或者针对特定对象所实施的添加行为,应当以他罪论处,故不宜与掺入行为并列在本罪的罪状表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