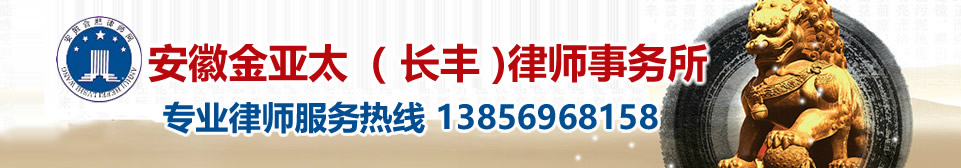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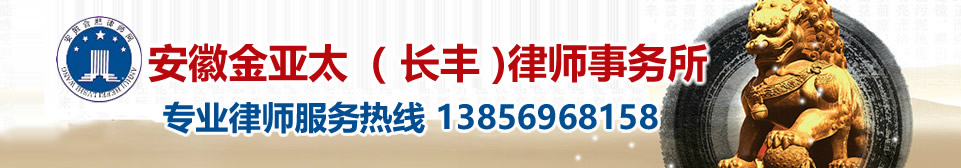
(一)新型盗窃罪导致的新问题之一:犯罪对象的再认识
由于新型盗窃罪在本质上属于非数额型盗窃罪,“非数额型”不仅指的是行为方式,而且关系到对行为对象的界定,这就导致了如何认识盗窃罪犯罪对象的问题。
传统上认为盗窃罪是数额型犯罪,因此主要是从财物的交换价值(客观的经济价值)角度来理解盗窃罪行为对象。比如,有观点认为“作为盗窃对象的财物应当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而且所谓经济价值应是指物品客观的、可以货币形式予以体现的属性。”然而,由于新型盗窃罪的定罪标准主要是基于行为方式而非犯罪数额,如果仍然将盗窃罪中的财物界定为具有某种经济价值的物品则不符合立法本意。因为,经济价值必然导致数额计算问题,而根据新的法律规定,数额并非是盗窃罪成立的必要条件,因此,经济价值不必然是犯罪对象的价值属性。
除了交换价值(客观的经济价值),具有使用价值(主观价值)的财物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比如某些纪念品(如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身份证等,本身不一定具有经济价值,但对所有人、占有人具有使用价值,因而应当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二)新型盗窃罪导致的新问题之二:犯罪门槛的再审视
1.“选择性执法”问题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行之后,醉酒驾驶的入罪标准曾被广泛争论,其中反对将醉驾行为纯粹客观入罪的论点之一便是选择性执法问题,在新型盗窃罪的法律适用中亦可能存在该问题,有学者即认为“不分轻重将‘扒窃’治罪,扩大了打击面,可能导致警方‘选择性执法’。”
事实上,不仅是在“扒窃”中,对于“携带凶器盗窃”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此类犯罪行为中,如果盲目地以行为本身与法律规定的契合作为定罪的标准,便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
2.刑法第13条但书的介入
关于犯罪概念,我国刑法第13条后半段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此即为我国刑法中的但书规定,其实质上体现的是社会危害性的出罪功能。
自从罪刑法定原则于1997年在我国刑法中确立以来,就一直有学者认为“但书”条款在司法中的适用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形式正义的要求,因此质疑但书条款及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合理性。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对社会危害性可能造成对罪刑法定的破坏从而侵犯人权的担忧。
事实上,但书条款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冲突。首先,“但书”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是一致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双向功能,同时起着扩大与缩小刑法打击范围的功能,而但书条款强调的是出罪的方面,实际上是通过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从而实现缩小刑法打击范围、保障人权的功能;其次,但书条款体现了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排除在判断罪与非罪时对行为从实质方面进行考察。如有学者认为,“形式正义有时与支撑其本身的基础——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存在矛盾。例如依照形式的犯罪概念,则很难避免这样的冲突:某行为原本没有社会危害性,甚至对社会有益,但如果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也要定罪处罚,何来人权保障?”虽然此观点有失极端,但却清楚地反映了社会危害性理论存在的必要性。本文来源于:www.xs180.cn